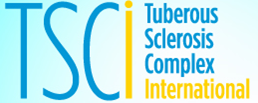罕见疾病关乎民族人口健康 相关立法困难重重
儿子4岁时,高琪(化名)夫妇就发现其走路异常,随着年龄增长到今天根本无法坐起,高琪夫妇20多年来辗转跑遍了中国各地的著名医院,但至今没有弄清楚儿子得的是什么病。
绝望真正彻底笼罩这个家庭,是10年之后出生的女儿在其5岁时出现与哥哥同样的症状。
“我们家也没有这样的遗传病,查不清孩子的病,我总是不太甘心。”将届花甲之年的高琪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得到一个真相。
困境:患者或没药治或治不起
在我国台湾地区,“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生了两三个有同样疾病的小孩。如果不去教育,不去提供福利吸引,让行政系统掌握到它的数量和他们的婚育规划,不断蔓延,最终政府还是要埋单”。
台湾地区罕见病“立法”重要推动者 曾敏傑教授,今年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罕见病学术研讨会上称,“罕见病是个公共健康的问题”。
研究社会学的曾敏傑投入推动罕见病“立法”中, 是一个意外。
上世纪90年代,他的儿子出生时得了一种很罕见的疾病。
一次,曾敏傑带儿子回台湾过暑假,孩子突然发病,情况紧急,但是医院告知,目前台湾没有任何医生和药物可以治疗这种非常罕见的代谢性疾病,惟一可救急的是去找台湾一位女士,她手上有从国外采购回来救助其自己孩子的药物。
“目前国内的罕见病患者绝大部分也面临两种困境:要么是没药可治,要么是有药治不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华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很多病没研发出来药,有药的又太贵,比如戈谢氏病,采用酶替代疗法,正常费用每月将近20万元,有几个家庭负担得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生罗小平,长期从事临床医学研究,他认为现状并不乐观,我国卫生机构、医药企业和医务人员对罕见疾病的认识和诊断水平非常低,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疾病,但没有得以诊断,更谈不上治疗,国内也没有一家企业研制出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
曾敏傑以亲身经历介绍了罕见疾病家庭所遭遇的困境:病人的压力来源于没有资讯、没有治疗医生;统计数据显示罕见病的确诊时间很长,常常是不断地转诊、误诊、再转诊,像高琪,几十年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也并非极端个例;即使最终确诊,药物也很难找到,没有药企有动力去进口需求极少的药物;经济上的负担尚且是最后一步的问题。
“种种困难都凸显罕见病人的困境,加上随时面临死亡风险,压力非常大。”一直致力于罕见病救助的曾敏傑深有感慨。
意义:立法不只为少数人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至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称之为罕见病,但各个国家和地区规定的发病率并不一样。国际上确认的罕见病有五六千种,约占人类疾病的10‰。若按此比例,我国各类罕见病患者超过千万人。
一般公众对罕见疾病几乎没有概念,基于中国文化心态,罕见病患者多数选择“躲在阴暗的地方自己独自去奋斗”。公众多认为,比千分之一还低的概率距离自己太过遥远。
而事实上,罕见疾病是个“公共性议题”。
曾敏傑介绍说,罕见疾病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风险。因为每个人身上有2.5万组基因,平均每人都有5至10个缺损基因,如果配偶双方的缺损基因撞在一起,罕见疾病就会发生,这种概率在非近亲通婚的情况下非常低,但巧合仍然会自然地产生。
我国台湾地区一家机构当年在游说“立法”时, 更多地是从上述角度论证的。“对罕见病人提供照顾和帮助,是着眼于整个民族人口的健康繁衍过程中必要的投资,诊疗成本的考虑只是救助,而当把问题看成是每一个健康人结婚怀孕过程中的风险时,国家就应该将人口品质提到更高位阶的关注”。
中华慈善总会罕见病救助办公室对一百多名戈谢氏病患者调查后发现,大部分患者来源于农村。在农村或者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当地人对罕见病可遗传不了解,因此缺乏防范意识,久而久之,“当地的人口素质肯定受到影响”。
曾敏傑认为,罕见病发生后的救助是下游问题,而教育与预防是上游问题,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第二胎或者第三胎还那么倒霉,实际上如果隐性基因已经存在,每一胎都是风险很大的(1/4甚至达到1/2), 数量不受控制地蔓延最终仍然是政府埋单。“在上游投资绝对比在下游投资成本低得多,而且更人道”。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给立法的触动是很大的,否则我们往往把这样的法律作为一种涉及少数人的规定,继而将它当成是边缘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全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教授认为,对罕见病立法必须有清醒的出发点。
现状:无政策无法律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清华大学的会议上称,自己在卫生部工作20多年,了解罕见病的概念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他坦承:“在罕见病的政策方面,目前我国还是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大背景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际上,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制定有罕见病救助专项法律,比较早的有澳大利亚和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西和古巴等发展中国家也早已颁布相关法律。
王晨光认为,法律对于常规的现象还是有所规制的,但是对一些特殊的情况,应对非常仓促和不足,尤其目前在罕见病的相关法律制度设计方面,远远滞后于现实社会的需要。
“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政策,孤儿药(罕见病用药)还面临着国外有却进不来,国内生产又存在制度障碍的问题。”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董艳峰向《法治周末》记者指出目前的双重困境。
比如孤儿药没有足够的临床样本去试验而无法上市,即使研发出来,也没有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目前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规范药品进口的条款,又没有为孤儿药提供“绿色通道”,“这些都加剧了罕见病无药可治的困境”。董艳峰认为。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研究所黄尚志,则用自己多年做产前诊断的经历来叙述法律政策缺失的困境。
2002年,我国就颁布了《产前诊断管理办法》,但7年之后“还是这样的水平”,单基因诊断不被法律管辖,医院不让做,但是老百姓有需求,偷偷求我们做,于是我们就以研究的名义打“擦边球”,出了事情就是非法。“我们的活儿干得如此艰难。20年前我就跟卫生部反映过要求,当时说给政策,但是现在政策在哪儿呢?”
路径:不求一步到位
从2006年起,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罕见病立法提过议案提案,其中,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维芳和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曾联合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专门提出制定罕见病防治法的议案。
8次参加全国“两会”的本届政协委员李定国称,各个部门对提案议案的态度都很诚恳,但是回答令人不甚满意。
有人提到,目前国内一般人的普通疾病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这个时候提及罕见病为时过早。
“从一般到特殊确实是规律,但现在也已经到了关注罕见病的时候了,不能等一般问题彻底解决好再关注罕见病。”清华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申卫星对《法治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
宋华琳认为,“事实上,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我们不可能永远指望跨国公司的捐助,更重要的是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有学者认为,基于我国的人口基数,中国立法的最大出发点,“应该首先立足于排队”,急需的疾病先入,有一些疾病只能后入。
卫生部专家组成员翟晓梅教授表示,仅仅根据疾病的发病率来判定其是否能够得到医疗是不公正的,但鉴于我国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考虑通过卫生部、人社部、民政部等相关部门制定部门规章,甚至是一种行政规定,来尽快解决问题。
曾敏傑指出,应将罕见病纳入了全民健康保险,“一开始如果全民健保同意纳入,也不会去'立法’, 最终'立法’确定,使位阶在下面的全民健保跟着埋单”。
但对于罕见病是否纳入医保,各国有不同作法。巴西是纳入联邦报销目录中全额报销。有学者认为,罕见病用药昂贵,很难一步进入,当务之急是先建立一个合理的费用支付机制,将来逐步实现医保纳入。
中国的人口基数与罕见病用药的数额容易造成财政负担的担忧,但事实上,据统计,有70%至80%的罕见病即使确诊,也没有能够用于治疗的药物。协和医院医生透露,有很多罕见病人出生没多久就过世了。
“每个国家和地区对罕见病的处理方式都不是固定的,这个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但回应的方式会受到时空和政治、经济、环境、制度的影响,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对话。”结束发言时,曾敏傑如是说。
【作者:陈霄 陈磊 来源:法治周末